我的家乡,是地图上一个需要用放大镜才能勉强找到的小镇。一条主街从东到西,走完用不了一袋烟的功夫。镇子被群山温柔而固执地环抱着,天空被裁剪成规整的方形。这里的生活,像一口古老的井,井水波澜不惊,映照着祖辈辈几乎一模一样的面孔和命运。我的父亲,是镇上一家老式纺织厂的维修工,他的世界被机油、扳手和那些永不停歇的机器轰鸣声填满。他的期望很简单,也很坚硬:读完职高,顶替他的岗位,然后娶妻生子,像一颗牢固的螺丝,拧在这台庞大的、名为“生活”的机器上。
有很长一段时间,我以为这就是我全部的未来。我甚至已经能闻到那车间里特有的、混合着棉絮和铁锈的气味,那气味仿佛已经提前渗入了我的肺叶。现实像一条冰冷的铁链,一头拴着厂房的铁门,另一头,就拴在我的脚踝上。我每向前试探一步,都能听见它哗啦作响的警告。
转折发生在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。我在父亲堆满杂物的工具箱底层,发现了一本被翻得起了毛边的《国家地理》。封面已经脱落,内页泛黄,散发着一股霉味。我随手翻开,一幅摄影作品猛地攫住了我——那是在辽阔无垠的戈壁滩上,一棵形单影只的胡杨树,它的枝干以一种近乎痛苦的姿态扭曲着,伸向湛蓝得令人心碎的天空。图片下的文字写着:“生而一千年不死,死而一千年不倒,倒而一千年不朽。”
那一刻,我心脏里那头沉睡的兽,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。我忽然无法忍受头顶这片被屋檐切割成方块的天空,我渴望看到戈壁的辽阔,渴望触摸沙漠的风沙,渴望成为那棵胡杨,哪怕孤独,也要向着天空,自由地伸展。一个清晰无比的念头,像闪电一样劈中了我:我要离开这里,我要去学摄影,我要用镜头,去记录下这个世界上所有被遗忘的、倔强的生命。
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父亲。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,空气黏稠得如同糖浆。他坐在昏暗的灯光下,久久没有说话,只是用力地抽着烟。烟雾缭绕,他的脸藏在后面,看不真切。最后,他掐灭烟头,声音嘶哑,像砂纸磨过生铁:“摄影?那能当饭吃?咱家什么条件,你不清楚?别想那些没边儿的事。”
“没边儿的事”。这四个字,像四颗钉子,把我那颗刚刚沸腾起来的心,牢牢地钉在了现实的十字架上。母亲在一旁偷偷抹眼泪,她的担忧是具体的,是柴米油盐,是街坊四邻的闲言碎语。那条现实的铁链,不再是哗啦作响的警告,它骤然收紧,勒进了我的皮肉,让我感到了真切的、令人窒息的疼痛。
我妥协了。我去了那所职高,学的是机械加工。我的日子被车床、铣床和无穷无尽的图纸填满。我的双手,本该去触摸相机快门、调整焦距的,如今却沾满了乌黑的油污,布满了细小的划痕。白天,我像一具空壳,重复着规定的动作,听着机器的轰鸣。可每到夜晚,那本《国家地理》里的景象,那棵胡杨的影子,就会在我眼前清晰地浮现。理想与现实,在我身体里剧烈地撕扯着,我感觉自己快要被撕成两半。
真正的爆发,是在我职高毕业,正式进入父亲那家工厂的第三个月。那一天,我负责操作的那台老式机床突然卡死了。我像父亲教我的那样,俯下身,用尽全身的力气去转动一个巨大的飞轮。汗水迷了我的眼睛,油污沾满了我的工装。就在我用力的瞬间,飞轮猛地松动,我的手背被旁边一个尖锐的凸起划开了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。
鲜血瞬间涌了出来,滴在冰冷、灰暗的水泥地上,开出几朵诡异的花。那一刻,肉体上的剧痛远不及心里的绝望。我看着那摊血,仿佛看到了我未来几十年的人生——它将和这摊血一样,无声无息地渗入这灰色的地面,最终干涸,消失,不留一丝痕迹。一种巨大的恐惧攫住了我,比疼痛更甚千百倍。
我被工友送去镇上的卫生所包扎。回来的路上,我没有直接回家,而是鬼使神差地走到了镇子边缘的小山丘上。站在那里,可以俯瞰整个小镇。夕阳正在西沉,把它最后的光辉涂抹在那些低矮的屋顶和工厂的烟囱上,给这个沉闷的世界短暂地镀上了一层虚假的金色。我看着那条熟悉的主街,看着那些像蚂蚁一样忙碌、归家的人们,看着我家那扇小小的窗户里透出的、微弱的灯光。
我的心里,有两个我在激烈地争吵。
一个说:“认命吧,这就是你的生活。安稳,踏实,有什么不好?”
另一个在呐喊:“那你呢?真正的你呢?就要死在这里了吗?”
风从山的那边吹过来,带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。我闭上眼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当我再次睁开眼时,目光越过了脚下的小镇,投向了更远处,那连绵的、在暮色中呈现出黛青色的山峦。山的那边是什么?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,如果我现在不迈出这一步,我这一生,都将被困在这片山峦围成的井底。
那个夜晚,我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、也是最艰难的决定。我没有和父亲争吵,也没有再试图去说服母亲。我只是默默地开始行动。我利用一切下班后的时间,去镇上一家小网吧帮人看店、修电脑,换取微薄的报酬。我戒了烟,拒绝了所有不必要的聚会。我把每一分钱都小心翼翼地存起来,那不再仅仅是钱,那是我一片一片为自己铸造的、挣脱铁链的钥匙。
这个过程,缓慢得令人心焦。疲惫是常态,孤独是伴侣。很多次,我看着存折上缓慢增长的数字,感到前所未有的渺小和无力。但每当这时,我就会想起手背上那道已经结痂的伤疤,想起那本《国家地理》,想起那棵胡杨。它们像黑暗中的灯塔,用微弱而坚定的光,支撑着我,不要倒下。
一年零四个月后,我攒够了一笔钱,刚好够买一张去远方的火车票,和一台二手的、但性能完好的单反相机。
离开的那天清晨,天还没亮。我将一封长长的信,放在了家里的饭桌上。信里,我没有讲任何大道理,只是写下了我看到那棵胡杨时的震撼,写下了我在车间里划伤手时的绝望,写下了我对山那边世界的渴望。我告诉他们,我不是逃离,我只是去寻找。我向他们保证,我会照顾好自己。
我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,里面装着那台相机和几件换洗衣服,轻轻推开了家门。晨雾像一层薄纱,笼罩着沉睡的小镇。街道上空无一人,安静得只能听见我自己的心跳声。我一步一步,走得很慢,却很坚定。那条曾经沉重无比的铁链,在我身后发出最后的、清脆的断裂声。
当我终于踏上那列绿皮火车,看着窗外熟悉的景物开始缓缓向后移动,加速,最终变成模糊的线条时,泪水毫无征兆地汹涌而出。那不是悲伤的泪,而是一种混合了巨大委屈、艰难挣脱和无限憧憬的复杂液体。它们畅快地流淌着,仿佛要冲刷掉过去所有积压在心里的憋闷。
火车轰鸣着,驶出了站台,驶出了小镇,一头扎进了群山的怀抱,然后,义无反顾地,穿过了那道我以为永远无法逾越的山隘。
那一刻,我知道,那个被现实阻碍的脚步,终于,被我迈开了。前方,是未知,是风雨,但也一定是,属于我自己的,辽阔人生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芒果经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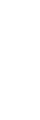 芒果经典
芒果经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45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35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35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32)
4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04)
5从外卖员到创业老板,他用汗水换来了成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