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拧开瓶盖,一股浓烈又朴素的酒香冲出来,带着点焦糊的甜味儿。就那么一瞬间,我忽然想起了我爸——他已经走了快十年了。
我爸也爱从出差的地方带酒回来。八十年代末,他第一次去北京,回来时小心翼翼地从行李箱掏出个玻璃瓶,那是罐红星二锅头。他眼睛发亮地跟我妈说:“这酒可有名了,毛主席都喝过!”那天晚上,他炒了盘花生米,倒了小半杯,咂了一口,皱皱眉:“嚯,真冲!”然后又笑了,“但够劲儿。”那是我第一次见我爸喝酒,他平时不喝的。
后来他出差多了,家里的酒柜渐渐丰富起来。从山西带回的汾酒,清冽绵长;从陕西带的西凤,带着股特别的凤香;还有江苏的洋河,安徽的古井贡……每瓶酒都配着一个故事。他不是品酒师,说不出什么“前调中调后调”,只会用最朴实的语言描述:“这个顺喉”“那个烧心”“这个喝完浑身暖和”。
2003年他去四川,背回来一坛五斤装的泸州老窖。那坛子粗糙得很,坛口用黄泥封着。他得意地说,这是直接去酒厂打的,比市面上的好。那天他特别高兴,叫了几个老同事来家里,就着麻辣兔头,一杯接一杯。我躲在门后偷看,看见他脸红红的,说话声音越来越大,最后唱起了年轻时常唱的老歌。那是我记忆中他最快乐的夜晚之一。
其实现在想想,我爸带回来的哪里是酒啊。那是他第一次坐飞机的兴奋,是他见识了外面世界的新奇,是他想与家人分享的所有见闻。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,不善于表达感情,就用这些来自远方的液体,诉说着他的经历和牵挂。
记得有一回,他从山东带回即墨老酒,黑褐色的,倒在碗里像中药。我妈嫌苦,他却很认真地用小炉子温热了,加进红糖,端给我妈:“听说女人喝这个好。”那一刻,我看见我妈眼眶有点湿。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,酒也可以这么温柔。
最后一次他带酒回来,是2013年春天,从湖南带了一小坛鬼酒。那时他已经病了,很瘦,但眼睛还是亮的。“这酒有意思,”他说,“听说工艺很特别。”那坛酒,他只喝了一次,说味道太重,受不了。剩下的就一直放在酒柜里。
他走后,整理遗物时,我望着那满柜子的酒,每一瓶都记得来历,记得他当时的神情。我妈说扔了吧,都过期了。我舍不得,最后留下了那瓶即墨老酒和那坛鬼酒。偶尔想他了,就打开柜子闻闻,酒香还在,虽然淡了,但那是时间的味道,是爸爸的味道。
今晚,我倒了小半杯老张带来的包谷烧。金黄色的液体在杯中晃动,闻起来有阳光的味道,像是晒过的玉米粒在舌尖化开。入口很烈,但咽下去后,喉咙里留下淡淡的甜。
我突然明白了,我爸带回来的从来都不是酒。是一个男人笨拙的爱意,是他看过的风景,是他走过的路,是他想说又说不出口的“我想你们了”。他把一个个陌生的地名,变成家人舌尖上的记忆;把他乡的滋味,酿成了我们共同的故事。
这杯包谷烧,和我爸当年带回来的所有酒一样,最终都成了同一种味道——那是家的味道,是牵挂的味道,是一个出门在外的人,总想着把远方带一点给亲人的心意。
酒会喝完,但装酒的瓶子我一直留着。那些粗糙的、精致的、土气的、华丽的瓶子,站在书架上,像是爸爸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的地标。现在,我要把这个贵州的士陶瓶也放上去,让它和我爸的那些瓶子站在一起。
也许有一天,我也会去很远的地方,也会给我的孩子带一瓶当地的酒。到时候,我要告诉他这些瓶子的故事,告诉他爷爷是怎么用一瓶瓶酒,把整个世界带回家的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芒果经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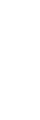 芒果经典
芒果经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43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32)
2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32)
3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31)
4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03)
5从外卖员到创业老板,他用汗水换来了成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