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到去了他家。
那是初秋的下午,他打电话说来接我:“来家里吃个饭吧,我炖了排骨。”声音里带着笑。我们认识三年了,却是第一次去他家。路上我一直在想,该把那个新买的玻璃小鹿放在哪里——那是我上周在旧货市场淘的,通体透明,鹿角上有一点金粉,在阳光下会闪闪发光。
他家在五楼,老式居民楼,楼梯窄而暗。但一开门,满屋子的阳光哗地涌过来,让人眼前一亮。客厅不大,却格外整洁,米色的沙发,原木的餐桌,一切都井井有条。最吸引我的是那排朝南的窗——整整三扇落地窗,外面是小小的阳台,秋日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,在地板上拉出长长的光影。
我的目光不自觉地寻找着窗台。那是很宽敞的大理石台面,被阳光晒得微微发暖。可是,上面空荡荡的,什么都没有。
真的,什么都没有。
没有常见的绿植,没有随手放的钥匙零钱,没有装饰性的花瓶,甚至没有一丝灰尘。它就那样赤裸裸地暴露在光线下,光滑得让人不知所措。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包里的玻璃小鹿,它在我手心微微发烫。
“你先坐,排骨马上好了。”他系着围裙从厨房探出头来,笑得自然。
我应了一声,假装随意地走到窗前。窗外是几棵梧桐树,叶子正渐渐变黄。多好的窗台啊——我在心里感叹。要是摆上我的小鹿,早晨的阳光照过来,一定会在地板上投下七彩的光斑;要是再放一盆绿萝,藤蔓可以顺着窗框爬上去;要是摆几个相框,放些旅行的照片...
可它就这样空着。空得彻底,空得坚决。
吃饭的时候,我终究没忍住:“你家窗台上怎么什么都不放?”
他夹了块排骨给我,笑了笑:“习惯了。我觉得这样挺好,干净。”
“可是...”我想说这样多浪费啊,窗台不就是用来堆放回忆的地方吗?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毕竟这是他的家。
那顿饭吃得很愉快,我们聊工作,聊最近看的电影,聊共同的朋友。可我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飘向那个空荡荡的窗台。阳光慢慢移动,从餐桌移到沙发上,窗台的影子被拉长,却依然空着。我的小鹿在包里沉默着,最终没有拿出来。
后来我又去过他家几次。春天去的时候,窗台空着;夏天去的时候,窗台还是空着。我渐渐明白,那不是疏忽,不是暂时,而是一种选择。他家的窗台,就是那样一个存在——它接纳阳光,接纳风雨,接纳窗外的一切风景,却拒绝任何人为的装饰。
有一次下大雨,我刚好在他家。雨水猛烈地敲打着玻璃窗,窗台因为温差蒙上了一层水汽。我看着他站在窗前看雨,背影安静。那一刻我突然懂了,这个空着的窗台,或许正是他内心的映照——他不需要任何外物来定义这个空间,窗台就是窗台,阳光来了又走,雨下了又停,一切都自然发生,自然结束。不需要小鹿,不需要绿萝,不需要任何证明“我来过”的痕迹。
这让我想起自己的家。每一个窗台都挤得满满当当:书房窗台是各种捡来的石头,卧室窗台摆着朋友们送的小玩意儿,厨房窗台则被多肉植物占领。每一个物件都在诉说着一个故事,标记着一段时光。我总以为,这样才是生活,才是记忆该有的样子。
可他的空窗台,却在无声地告诉我另一种可能:有些空间,本就该空着;有些时刻,本就该安静地流过。
去年冬天,他出差半个月,把钥匙留给我,让我帮忙给花浇水。那是我第一次独自待在他的空间里。下午三四点的光景,冬日的阳光稀薄而珍贵,正好照在空窗台上。我站在那儿,看着光线下微尘飞舞,突然理解了这种空的意义——它不是匮乏,而是丰盈;不是拒绝,而是包容。它包容了最纯粹的光,最干净的风,最完整的景色。
我的玻璃小鹿终究没有留在那里。它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,每天迎着阳光闪闪发亮。但我很感激那次“无处安放”的经历,它让我明白:真正的印记,不一定非要具象地留在某个地方。就像那个下午,我站在他家的空窗台前,看着阳光一寸寸移动,那种安静而充盈的感觉,已经比任何小摆件都更深地留在了我的心里。
如今再去他家,我已经不再想着该放什么在窗台上了。偶尔阳光特别好时,我们会一起站在那儿喝茶,看楼下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,看天空的云慢慢飘过。那个空着的窗台,成了最恰到好处的留白,让所有的光线和风景都找到了最好的归宿。
而我也依然保留着送朋友小摆件的习惯,只是不再执着于窗台——有的放在了书架上,有的摆在了玄关,还有的,就让它一直留在我这里。毕竟,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不一样的窗台,有的适合装满回忆,有的,就适合那样空着,让阳光直接照进来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芒果经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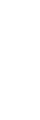 芒果经典
芒果经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43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32)
2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32)
3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31)
4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03)
5从外卖员到创业老板,他用汗水换来了成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