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爸——”我朝客厅方向喊了一声。
没有回应。音乐太响了,我的声音像一粒沙子被卷进轰鸣的巨浪,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我把包挂在玄关的衣架上,换了拖鞋,沿着走廊慢慢往里走。越靠近客厅,音乐越是震得人心头发麻。走到客厅门口,我看见他了——我的父亲,就坐在那张褪色的布艺沙发上,背对着我。
他完全没有察觉我的到来。花白的头发在午后的光线里泛着柔和的光,肩膀随着音乐的节奏微微晃动。我站在原地,看着他的背影,突然不忍心打扰。
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这样听音乐。
在我记忆里,父亲总是安静的。他年轻时在工厂做技术员,每天和机器打交道,养成了轻声说话的习惯。晚上看电视,音量永远控制在刚好能听见的程度。母亲常开玩笑说,咱们家连钟摆声都嫌吵。
可此刻,八十多分贝的音乐正充满整个空间。罗大佑在唱:“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”,每一个字都像用尽全力喊出来的。
我绕到沙发侧面,这下能看见他的正脸了。他闭着眼睛,右手在膝盖上轻轻打着拍子,嘴唇无声地动着,像是在跟着唱,又像是在默念歌词。他脸上有种我从未见过的神情——不是平静,不是喜悦,而是一种近乎虔诚的专注,仿佛正进行着某种重要的仪式。
“爸!”我提高音量,几乎是在喊了。
他猛地睁开眼睛,看见我,愣了一下,然后慌慌张张地去找遥控器。“你回来了啊?我没听见。”他边说边调小音量,世界突然安静下来,安静得让人有些不适应。
“没事,您听吧。”我说。
他摇摇头:“太吵了,影响你。”
那天晚饭时,我问起那首歌。父亲扒拉两口饭,轻描淡写地说:“就是突然想听了。”但母亲后来告诉我,那天是父亲一位老朋友的忌日。他们年轻时一起在工厂文艺队,最爱弹的就是这首歌。
“你李叔叔走五年了。”母亲叹了口气,“他们当年啊,抱着吉他在厂院里唱歌,下面坐满了年轻人。”
我这才明白,父亲不是在听音乐,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回到某个时刻——那时他们还年轻,歌声里有整个夏天的风,有对未来毫无保留的相信。而如今,他需要把音量开到最大,才能勉强听见逝去岁月模糊的回声。
从那天起,我开始留意父亲听音乐的习惯。他通常在周三下午和周六上午听——后来我知道,周三他曾和李叔叔一起排练,周六则是演出日。他听的歌很固定,就那么十几首,循环播放。《光阴的故事》《恋曲1990》《橄榄树》……都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歌。
有一次,我故意在他听音乐时走过去,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。他过了好一会儿才注意到我,然后像做错事的孩子,急忙要调小音量。
“别关,”我按住他的手,“挺好听的。”
他犹豫了一下,点点头。我们就这样并排坐着,任由音乐将我们淹没。那次的歌是《橄榄树》,齐豫的声音空灵而遥远。我偷偷看父亲的侧脸,发现他眼角有细细的泪光。他没有擦拭,任由它们静静停留在皱纹里。
后来我查了资料,才知道这是很多老年人的共同体验——听力下降后,他们会不自觉地提高音量。这不只是为了听得更清楚,更是一种心理需求: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安静,当熟悉的声音一个个消失,他们需要某种足够响亮的东西来确认自己的存在,来填补那些突然多出来的空白。
但理解是一回事,真正接受又是另一回事。说实话,那些下午并不总是温馨的。有时我带着工作回家的疲惫,需要安静;有时我想看电视,却不得不退回自己的房间。每当这种时候,心里总会升起一丝不耐烦。
直到那个雨天的下午。
那天我感冒了,请假在家休息。父亲不知道,照例在客厅放起了音乐。头痛欲裂的我正准备出去请他关小一点,却在开门时停住了。
透过门缝,我看见父亲站在客厅中央,手里拿着什么。我眯起眼睛仔细看——那是一张泛黄的合影,他和李叔叔年轻时的合影。两个人勾肩搭背地笑着,背后是工厂的大礼堂。
音乐正在播放《闪亮的日子》。父亲跟着哼唱起来,声音不大,却异常坚定:
“我来唱一首歌,古老的那首歌
我轻轻地唱,你慢慢地和
是否你还记得,过去的梦想
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……”
他唱得并不好听,甚至有些走调。但那一刻,我突然理解了他为什么要开那么大的音量——他不仅要听见音乐,更要感受它。感受每一个音符的振动,感受旋律在胸腔引起的共鸣,感受那些被岁月稀释的情感重新变得浓烈。对他而言,这已经不是在欣赏,而是在打捞,打捞沉在记忆深处的点点滴滴。
我没有出去,轻轻关上门,回到床上。头痛依然,但心里某种坚硬的东西开始融化。我想起自己手机里存着的大学时常听的歌,那些曾经单曲循环无数遍的旋律,如今已经很久没有打开。不是不喜欢了,而是不敢——怕听见从前那个天真热血的自己,怕对照出现实的苍白。
原来,我们都用各自的方式,逃避着时光的无情。
从那天起,我和父亲达成了一个默契:每周三和周六,是他尽情听音乐的时间。我会提前安排好,要么出门,要么戴上降噪耳机。偶尔,我还会在他听完音乐后,和他聊聊那些老歌,聊聊他年轻时的故事。
他讲起1979年的文艺汇演,讲起他们自己组装的音响,讲起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。讲这些时,他眼睛里有光,整个人都变得生动起来。
上个月,我做了一个决定。我买了一套不错的音响送给他,并对他说:“爸,以后听歌用这个吧,音质更好。”
他摆弄着新音响,像个得到新玩具的孩子。当音乐从新音响里流淌出来时,他惊喜地睁大眼睛:“真的不一样哎,清楚多了。”
那一刻,我突然很想哭。我终于明白,这些年来,他开那么大音量,不是因为想要吵闹,而是他使用的老旧设备已经无法清晰地传达那些珍贵的声音。他不得不提高音量,来补偿设备的不足,来捕捉每一个即将消失在电流声中的音符。
现在,他依然每周听歌,音量依然比普通人家大一些,但不再像从前那样震耳欲聋。有时周末的下午,我会陪他一起听。我们不怎么说话,就静静地坐在沙发上,任时光在音乐中缓缓流淌。
就在昨天,听着《光阴的故事》,父亲突然说:“你李叔叔要是知道你现在这么有出息,一定很高兴。”
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,深深浅浅的皱纹,突然意识到:那些震耳欲聋的下午,那些我以为是他固执制造的噪音,其实是他对抗遗忘的方式。在巨大的音量里,逝去的人还没有走远,青春的激情尚未冷却,所有美好的时光都还栩栩如生。
而我很庆幸,在他需要这样巨大的声响来维系与过去的连接时,我最终选择了理解,而不是阻拦。生命中有太多声音会随着时间渐渐微弱,直至消失。如果有人需要调大音量才能继续听见,那我们唯一能做的,或许就是安静地站在一旁,见证并尊重这份执着。
毕竟,总有一天,我们也会老去,也会需要调大音量,才能听见青春的回声。到那时,我们一定会感激,曾经有人包容了我们的“吵闹”,就像包容我们内心深处,那个不肯老去的少年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芒果经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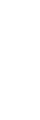 芒果经典
芒果经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43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32)
2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32)
3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31)
4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03)
5从外卖员到创业老板,他用汗水换来了成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