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这时,我看见了他。
一个老人,约莫七十多岁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,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。他站在离站台几步远的地方,不停地朝公交车来的方向张望,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焦急。每有车灯从远处亮起,他的身子就会微微前倾,等看清不是16路,又失望地退回去。
16路终于慢悠悠地进站了。大家自觉地排起队,我站在队伍中间。老人也赶紧走过来,排在最后。他不停地翻着口袋,先是上衣口袋,然后是裤子口袋,翻来翻去,脸色越来越慌。轮到他上车时,他站在投币箱前,手有些发抖。
“师傅,我、我的钱包好像丢了……”他的声音很低,带着浓重的乡音。
司机是个中年男人,面无表情:“没办法,规定要投币的。”
“我就到终点站,不远,”老人近乎哀求,“我儿子在那边工地干活,我给他送点东西。”
“人人都这么说,我要是都让上,公司要扣我钱的。”司机摇摇头,“您下去吧,别耽误后面的人。”
老人僵在那里,满脸窘迫。后面有人开始不耐烦:“快点啊,赶时间呢!”
我摸了摸口袋,正好有两枚硬币。那一瞬间,我几乎要开口说“我帮他付吧”。可就在这个念头闪过的同时,另一个声音在心里响起:万一他是骗子呢?新闻里不是常说这种骗局吗?再说,两块钱虽然不多,但也不能随便给人骗啊。
就这么一犹豫,司机已经关上了前门,只开了后门让其他人继续上车。老人被留在了站台上,隔着车窗,我看见他茫然地站在那里,像一棵突然被遗弃的老树。
车门“嗤”的一声关紧了。车子启动的那一刻,我看见老人抬起手,似乎想说什么,但最终什么也没说。他的身影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,最后消失在暮色里。
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,心里开始不是滋味。刚才那几分钟里发生的一切,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回放——他焦急的眼神,发抖的手,还有那句“我儿子在工地干活”。那个布包里装的是什么?也许是老伴做的饼,也许是孙子画的画,也许只是一件干净的换洗衣服。一个老人,大老远跑来给儿子送东西,却因为两块钱被拒之门外。
车开过两个路口,等红灯时,我看见路边工地上有几个戴安全帽的工人在收拾工具。其中一个年轻人站在高处,正望着我们这个方向。他在等谁吗?会不会就是那个老人的儿子?
我心里突然被什么东西揪紧了。那两块钱,对我来说不过是一瓶水钱,对他却是能否见到儿子的关键。我为什么没有帮他?因为怀疑,因为犹豫,因为那可笑的自保心理。
我想起自己的父亲。多年前,父亲来城里看我,也是坐公交车,也是因为不熟悉自动投币,在车上手足无措。当时有个姑娘帮他投了币,父亲感激了一路,回家后还反复念叨:“城里人真好。”那时我觉得这是件小事,现在才明白,对那个姑娘来说可能是举手之劳,对父亲来说却是这座城市给予的温暖。
而我,今天却吝啬了这份温暖。
车子继续往前开,窗外的灯火陆续亮起。每一盏灯下,都有一个等待的家吧。那个老人的儿子,在工地上劳累一天后,是否还在等着父亲的到来?而那个老人,现在又在哪里?是步行往工地走吗?要走多久?天黑路滑,他认得路吗?
这些念头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我,越缠越紧。我甚至想现在就下车,往回走,去找那个老人。可是车已经开出去很远,即便回去,他肯定也不在原地了。
到站了,我随着人流下车,却没有往家走,而是在站台的长椅上坐了下来。夜风吹在脸上,凉飕飕的。我望着16路车消失的方向,心里空落落的。
这件事过去好几个月了,我还是会经常想起那个老人。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,坐公交车时总会多备几个硬币。遇到过忘带零钱的学生,遇到过手机没电的年轻人,每次帮他们投币时,我都会想起那个黄昏,那个穿着蓝色工装的老人。
我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走到工地,有没有见到儿子。也许他赶在天黑前走到了,父子俩在工棚里分享着布包里的东西;也许他迷路了,很晚才到;也许他根本就没能走到,半路又返回了……
这些“也许”成了我心里的一根刺。它提醒我,有些善意不能等待,有些犹豫会成为永远的遗憾。两块钱的善意,我欠那个老人的,也欠那个在工地上等待的儿子。更重要的,我欠那个曾经相信“城里人真好”的自己。
城市的夜晚依然灯火通明,每盏灯下都在上演着各自的故事。而那个黄昏的故事,成了我心头一道浅浅的疤痕——不痛,但永远在那里,提醒着我:下一次,当有人需要那两块钱的善意时,不要再犹豫。因为你看不见的是,这两块钱的背后,可能是一个父亲想要见到儿子的全部期盼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芒果经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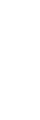 芒果经典
芒果经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43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32)
2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32)
3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31)
4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03)
5从外卖员到创业老板,他用汗水换来了成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