办公室里新来的小伙子,才二十三岁,敲键盘的速度快得让人眼花缭乱。他嘴里时不时蹦出几个新词儿,什么“云原生”、“容器化”、“微服务治理”,我听着耳熟,细究起来却又模模糊糊。开会的时候,他侃侃而谈,眼神里是那种我年轻时才有的、对技术的绝对自信和光亮。而我,更多时候是沉默,是下意识地摩挲着手里那用了多年的保温杯。一种无形的压力,像冬天的寒气,从脚底一点点往上爬。
我干了快二十年IT了。从最初跟着师傅学装系统、排网线,到后来没日没夜地啃Java,做项目,一步步成为团队里的技术骨干。那些年,服务器就像我的老伙计,哪个端口出问题,哪段代码有隐患,我闭着眼睛都能摸个大概。我以为,这套手艺够我吃到退休了。
可时代变得太快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我熟悉的那个“稳态”的IT世界,变成了一个“敏态”的、飞速旋转的陀螺。框架几个月一更新,技术栈一年一换代。我开始需要花更多时间去查阅文档,去理解那些新概念。以前是我带新人,给他们讲架构,讲设计模式;现在,偶尔反而要悄悄去问那些年轻人,“这个框架的坑在哪儿?”“你们说的那个DevOps流程,具体是怎么跑的?”
那种感觉,很不是滋味。不是嫉妒,是一种更深层的恐惧,怕自己被这趟高速列车甩下去,怕自己积累了半辈子的经验,一夜之间变成一张废纸。我看着那些精力充沛、学习能力像海绵一样的年轻人,他们可以为了一个技术难点通宵达旦,他们对新事物有着天生的亲近感。而我,下了班要操心孩子的功课,要打理家里的琐事,精力被生活分割得七零八落。学习的脚步,越来越沉重。
我知道,不能这么坐以待毙。挣扎了很久,我决定,学!就从那个最火、听起来也最颠覆的“容器化”技术开始。
那真是一段“自虐”的日子。我把家里书房变成了第二个办公室。晚上九点,安顿好孩子睡下,才是我的学习时间。打开电脑,对着官方文档和网上找来的教程,一行行命令地敲,一个个概念地理解。好多东西和我的旧有认知完全是两套体系,就像让你一个用惯了右手的人,突然开始用左手写字。脑子里的那根弦,绷得紧紧的。
记得有一次,为了搞明白一个网络联通的问题,我折腾到凌晨两点。屏幕上的错误日志红得刺眼,我像个没头苍蝇,在搜索引擎里一遍遍换着关键词。那一刻,巨大的挫败感袭来,我几乎要放弃了。我问自己:图什么呢?安安稳稳混到退休不行吗?
可一想到办公室里那些年轻人清澈又充满求知欲的眼神,一想到可能被时代无情地边缘化,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又上来了。我关掉浏览器,深吸一口气,重新回到命令行,从最基础的原理开始,一步一步地梳理。当第二天清晨,阳光照进书房,那个该死的容器终于跑通,并且成功连上数据库时,我几乎要从椅子上跳起来。那种久违的、攻克难关的喜悦,像一股暖流,冲散了所有的疲惫和自我怀疑。
就这么咬着牙,我慢慢掌握了容器技术,接着又向自动化运维、持续集成/持续部署(CI/CD)领域拓展。过程依然痛苦,但每一次小小的成功,都给我注入一点信心。我发现自己并没有真的老去,只是需要换一种方式奔跑。
也就在这个时候,公司启动了一个新项目,技术栈正好是我刚啃下来的这一套。领导找到我,说:“老李,这块你比较熟,带带新来的小陈吧。”
小陈,就是那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。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带他?我能带他什么?他可能懂得比我还前沿。一种微妙的、怕被比下去的心理又冒了出来。
第一次和小陈坐下来讨论技术方案,我尽量让自己显得从容。我讲着架构设计,讲着容器编排的选择,他听得很认真,不时点头。但当我讲到某个具体的技术实现细节时,他忽然抬起头,眼睛亮亮地看着我,问:“李工,这个地方,如果考虑到底层硬件的异构性和资源争抢,我们是不是应该加一层资源隔离的策略?我看过一篇论文……”
他问的这个问题,非常深入,直接戳到了潜在的性能瓶颈。我愣了一下,随即,我们俩就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。我分享了我过去在处理高并发、资源调度方面踩过的坑和总结的经验,他则提供了几种最新的、基于开源工具的实现思路。
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了。我带他的,不是那些最新的、他可能一搜就能搜到的命令和参数,而是我二十年职业生涯里,用无数个不眠之夜和项目教训换来的“经验”——那种对系统稳定性的直觉,对潜在风险的预判,对复杂问题抽丝剥茧的思维方式。这些,是书本和教程给不了的,是时间赋予我的、独一无二的财富。
而他从我这儿获取经验的同时,他也用他活跃的思维、对新技术的敏锐嗅觉,不断地“反哺”着我。他告诉我某个社区刚发布的优化方案,推荐了几个极客们都在用的效率工具。我们不再是简单的“师徒”,更像是一种“合作者”,一种“互补”的关系。
项目推进的过程中,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线上故障,服务间歇性卡顿,监控指标却一切正常。小陈和年轻人们尝试了各种最新的 profiling 工具,定位了半天,还是没有头绪。那天下午,我看着监控图表上那规律性出现的微小毛刺,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处理过的一个类似案例。那是一次由底层数据库连接池泄漏引发的“幽灵”问题,症状和现在极其相似。
我带着小陈,没有去追踪最新的日志,而是径直去检查了数据库中间件的连接数监控和历史查询队列。果然,找到了那个隐蔽的泄漏点。小陈看着修复后变得平滑的曲线,由衷地说:“李工,还是您经验老到,我们光在应用层打转了,没想到是基础设施层的老毛病。”
我笑了笑,没说话。但心里那块压了很久的石头,仿佛在那一刻被彻底移开了。我不再恐慌,也不再焦虑。
现在,我依然在不断地学习,只是心态完全不同了。我不再是为了不被淘汰而恐惧地学,而是为了能更好地和像小陈这样的年轻人合作,为了能继续在我热爱的这个行业里创造价值而主动地学。我组织团队内的技术分享,鼓励年轻人讲他们的新发现,我也乐于分享我的“陈年老坑”。我发现,当我打开自己,真诚地去交流和传递时,年轻人回报给我的是更多的尊重和信任。
回头看看这段路,我忽然觉得,我们这代IT人,就像是站在传统与变革桥梁中间的守桥人。我们熟悉来路,也看见了新的方向。我们曾经的恐惧,源于对未知的敬畏,也源于对自身价值的怀疑。但技术的浪潮,淘汰的从来不是年龄,而是固步自封的头脑。
手里那杯茶,温温的,正好。屏幕上的代码,在年轻人的指尖和我的注视下,流畅地运行着。窗外,是这个城市永不熄灭的灯火。我想,所谓传承,大概就是这样吧——不是简单的交付与接受,而是在奔腾的河流中,前浪与后浪的相互激荡,共同奔向一片更广阔的海洋。而我,依然是这条河流中,一朵有力而饱满的浪花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芒果经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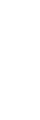 芒果经典
芒果经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43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32)
2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32)
3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31)
4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03)
5从外卖员到创业老板,他用汗水换来了成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