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家住在城西的老居民区,楼下有棵大槐树,少说也有三四十年了。每年夏天,蝉就趴在树上拼命地叫。他总爱说:“你听,这是夏天的声音。”说这话时,他正坐在阳台的藤椅上,手里摇着那把已经发黄的蒲扇。蒲扇边缘有些破损了,他用透明胶带仔仔细细地贴了好几道。
他是我的爷爷。
爷爷是个退休的语文老师,戴一副老花镜,镜腿用白胶布缠着。他说话慢悠悠的,就像他摇蒲扇的节奏,不紧不慢。每年蝉鸣最盛的时候,就是我们祖孙俩相处最多的日子。
傍晚时分,太阳还没完全落山,天边烧着橘红色的晚霞。爷爷会把藤椅搬到阳台,再给我搬个小板凳。我坐在他旁边,看着他泡茶——永远都是那个印着红双喜字的搪瓷缸,茶叶放得不多,水要滚烫的。他先吹开浮在上面的茶叶,小心地呷一口,然后满足地叹口气。
“来,爷爷教你背诗。”这是他最常说的话。
于是我就跟着他念: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”念到“蝉”字时,窗外的知了正好叫得起劲,像是给诗句伴奏。爷爷的眼睛会眯成一条缝,笑着说:“你看,古人早就听见了和我们一样的声音。”
有时他不教诗,就给我讲故事。讲他小时候在乡下,夏天和小伙伴们举着长竹竿粘知了;讲他们逮着了知了放在蚊帐里,听它吱吱地叫,结果半夜被吵得睡不着;讲知了要在地下待好几年,才能爬出来唱一个夏天。他说这话时,眼神会飘得很远,仿佛能穿过层层岁月,看见那个光着脚丫在田埂上奔跑的自己。
“所以啊,”他收回目光,用蒲扇轻轻拍着我的后背,“它们叫得再大声些也是应该的。等了那么久,总要尽情地唱一回。”
那时的我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些话,只是觉得爷爷的声音和着蝉鸣,有种让人安心的力量。
记得有一个特别闷热的晚上,停电了。整个小区黑漆漆的,只有月光朦朦胧胧地照进来。爸妈去楼下乘凉了,我和爷爷留在家里。他点起很久不用的煤油灯,火苗一跳一跳的,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。
“太热了,睡不着吧?”爷爷问我。
我点点头。其实更让我烦躁的是那些蝉,停了电,没有电风扇的嗡嗡声,它们的叫声显得格外刺耳。
爷爷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,他说:“你静下心来听,它们不是在瞎叫,是有节奏的。”
我屏住呼吸仔细听,果然,那些看似杂乱无章的鸣叫,其实有着起伏的节律——先是几只领唱,接着大批跟上,达到高潮后渐渐弱下去,停顿片刻,又重新开始。
“像不像大合唱?”爷爷笑着问。那晚,他破例没有教我背诗,也没有讲故事,我们就静静地坐在黑暗里,听着蝉鸣的潮起潮落。煤油灯的光把他脸上的皱纹照得格外深,可他的眼睛很亮,像把整个夏天的星星都装了进去。
后来我上了中学,暑假要补课,能陪爷爷听蝉的时间越来越少。他还是会坐在那个阳台,只是更多时候是一个人。妈妈说他经常望着槐树发呆,一坐就是一下午。
高二那年的初夏,爷爷住院了。去医院看他时,他精神还不错,拉着我的手说:“等槐树上的知了开始叫了,我就该出院了。”
可是蝉还没有开始叫,他就走了。
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失去亲人的痛。葬礼结束后,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样。直到夏天真正来临,第一声蝉鸣响起时,我才意识到具体少了什么——少了他。
现在的夏天,蝉鸣依旧。我坐在爷爷曾经坐过的藤椅上,学着他也泡一杯茶。茶叶在热水里慢慢舒展开,我吹开浮沫,小心地喝一口。蒲扇还挂在老地方,只是再也没有人用它给我扇风了。
我试着像爷爷那样静下心来听蝉鸣。起初还是觉得吵,但听着听着,竟真的听出了节奏。那些起伏的声浪里,我仿佛又听见他在教我念诗: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”声音温和而清晰,就像他从未离开。
有时邻居家的孩子会跑来问我:“姐姐,知了为什么叫得这么响啊?”我就会把爷爷告诉我的那些话说给他们听:它们在地下等了那么久,就为了这一个夏天,总要尽情地唱一回。
说完这些话,我自己都会愣一下—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我活成了爷爷的样子。
今年槐树上的蝉特别多,叫声也比往年更响亮。傍晚时分,我会搬两个小板凳到阳台,一个自己坐,一个空着。隔壁刚搬来的小姑娘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总多摆一个凳子,我想了想,说:“在等一个教我听蝉的人。”
其实我知道,他永远不会再坐在这里,摇着蒲扇,慢悠悠地喝茶念诗了。但他把听蝉的耳朵留给了我,把夏天的诗意留给了我。如今每一声蝉鸣里,都有他的影子。
蝉声依旧喧嚣,夏夜依旧闷热。只是在这熟悉的季节里,永远少了他的声音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芒果经典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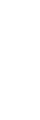 芒果经典
芒果经典
热门排行
阅读 (143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32)
2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32)
3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31)
4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03)
5从外卖员到创业老板,他用汗水换来了成功